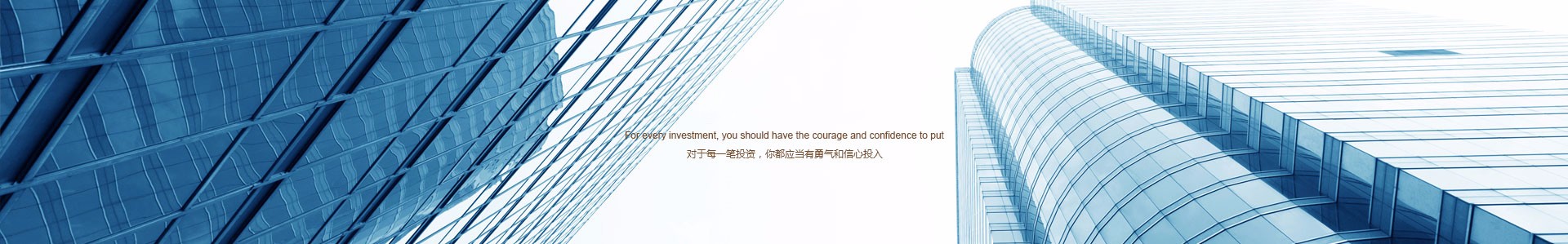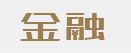为什么孩子PG电子官网- PG电子试玩- APP下载无法摆脱手机?
2025-10-30PG电子,PG电子官方网站,PG电子试玩,PG电子APP下载,pg电子游戏,pg电子外挂,pg游戏,pg电子游戏,pg游戏官网,PG模拟器,麻将胡了,pg电子平台,百家乐,捕鱼,电子捕鱼,麻将胡了2这是学者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观察到的状况。他在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心理学相关的课程,早在十年前,他就发现这一批孩子变了:他们在意情绪,在意细小的原则,却注意不到15米外的草坪正在变绿。越来越多人过于依赖手机,并被诊断为焦虑或抑郁。他做了一些研究,把原因归结为现实的退却——家长们过度紧张,不允许孩子随意出门玩耍,也不让他们自主探索外界。「玩耍式童年」的退场,使得孩子们对外界的想象充满危险,也就止步于防御与焦虑。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海特发现自己低估了手机类智能设备在影响年轻人心理上所起的作用。为此,他写作了《焦虑的一代》,进一步阐释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群体性心理危机。
在玩耍式童年退场之后,「手机式」童年成为主流。家长在现实世界中各种设限,但孩子们却在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里横冲直撞,年轻人是被保护在了安全的家里,但大量的在线时间让他们不再建立真实的友谊、睡眠不足、注意力分散,并且对手机成瘾。男孩们沉迷于电子游戏,女孩则饱受社交网络带来的焦虑困扰。
这是手机时代的系统性的难题。许多孩子最初注册账号的原因就是「不想被落下」,而一旦进入,「跟不上」的阴影就会始终笼罩着他们。在这种时候,父母质疑没收手机,也只会把他们推向更加被孤立的处境。
孩子沉迷手机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美国。在中国,这也变成了越来越多家长关切的问题。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一项针对12万名3~5岁儿童的调查显示,有将近1/3的儿童每天电子屏幕暴露时间超过2小时;另一项由华东师范大学牵头的研究显示,在排除了性别、年龄、体重这些因素的影响后,如果13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看屏幕的时间超过两小时,他们的情绪问题、行为困扰和社交适应困难,往往会更明显地增加。
面对沉迷于手机的孩子,父母能做些什么?在海特看来,这正是延续人类传统群体智慧的时刻。过去人们说「养育一个孩子要靠整个村庄的共同努力」,现在,家庭、科技巨头乃至整个社会也应该站在一起,为我们的下一代打造一个自由玩耍的空间。同时,大人们必须也意识到,孩子们并不是主动把现实世界让给手机的,只要有一点合力,哪怕只团结到了5个家庭,让孩子们可以自由结伴出门,结果都有可能不一样,而我们能做到的远不止这些。
第一个女孩叫埃米莉,14岁,喜欢用Instagram,但一旦开始在手机上刷Instagram,她就会进入一种焦虑又沮丧的状态。她的父母不得不在手机上下载好几个APP,专门去监控和限制女儿过度使用社交媒体。
这意味着什么呢?亲子战争开始了。埃米莉想办法黑进了她妈妈的手机,卸载了监管软件,并威胁他们,再敢安装,她就自杀。
这对父母试过为女儿报名夏令营,营里规定不能带手机和一切电子产品。6周后,他们接回女儿,发现她状态恢复了很多。他们也试过给埃米莉换一部老式的翻盖手机,让她不那么焦虑。但这些手段都是暂时的。给我讲完这段经历后,埃米莉的妈妈是这么下结论的:除非全家下定决心搬到荒岛上生活,否则埃米莉永远无法戒掉社交媒体和手机。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男孩,詹姆斯,患有轻度的自闭。他一直在学校适应得不错,还参加了柔道社团,直到新冠疫情来临,学校停课了。那时,他11岁,父亲给他买了一台游戏机。
游戏机的确立了功。詹姆斯玩得很好,也享受在里面的社交。但随着他对其中一个游戏上了瘾,他开始变得不对劲。「他变得抑郁、愤怒、懒惰,甚至也对我们发火。」他的爸爸说。父母决定没收游戏机,可詹姆斯很快就表现出了戒断症状,变得易怒,有攻击性。他还把自己锁进了房间,不肯出门。后来,詹姆斯的症状有所好转,但他的父母左右为难,网上这群伙伴对儿子来说来之不易,他们不想一刀切,但找到一个合适的度很难。
以上是我收到的父母来信中的冰山一角,当下,实在是太多父母都在讨论电子设备成瘾这件事了。不过,让我真正感到意外的,是《焦虑的一代》出版后,有如此多的母亲站了出来。父母们的绝望和恐惧,尤其是来自母亲的,是如此巨大,她们共享这些情绪。这本书能占据畅销榜榜首70周,也是因为妈妈们都在读它。我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在家庭中总是在扮演一个支持者的角色。但母亲不一样,她们和孩子的接触是更日常的,因此也更能切身感受到自己被孩子推远——他们进到了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而她被关在门外。
当然,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最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家长告诉我,自己的孩子出现了或轻或重的心理问题。这也符合我在大学任教的经历——我在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心理学相关的课程,大概从2014、2015年开始,我观察到这一代学生有明显的转变:他们更加脆弱,也更加焦虑。当时,我和记者格雷格·卢基亚诺夫讨论过这件事,后来还在《大西洋月刊》上撰写了相关文章《娇惯的心灵》,来讨论这场巨大的群体性心理危机。
我们一起做了从2008到2018十年的统计。数据上看,从2012年起,美国12~17岁的青少年患抑郁症的概率陡然攀升,2010-2015年的数据直接成「曲棍球棒」式增长,几乎增加到了之前患病率的2.5倍。孩子们的问题集中在「内化障碍」,也就是焦虑和抑郁上——与之相对应的是「外化障碍」,患者也会感到痛苦,但他们会向他人表现和发泄出来,传统来说,女性遭受内化障碍的比例更高,男性更受外化障碍困扰,但从这10年的数据来看,无论性别,内化障碍都有与日俱增的趋势。
这次心理大危机的发生范围也极广,任何性别、种族或社会阶层都没有幸免,我因此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大重构时期」。2018年,我们把《娇惯的心灵》拓展成书,其中的一章提到了手机——很多研究表明,玩手机玩得最多的孩子,也是抑郁最严重的那一群。但相关性不代表有因果,当时,我和卢基亚诺夫更多把着眼点放在了现实世界。
我们觉得,青少年更加敏感和脆弱,原因之一就是新一代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他们不允许孩子独自出门,学校和公园里的危险游乐设施也被拆除了。童年不再自由自在,现实被定义为「危险的」,非要从头武装到脚才能出门。
但在我们文章发表的第二天,《》就反呛了我们。他们刊登了一篇名为《青少年的焦虑问题,无须小题大做》的文章,试图说明当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只是看似严重。可能是现在的人们更加坦诚也愿意自测、可能是他们喜欢小题大做、也可能就是我们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1世纪开局本就不利:我所在的美国接连发生了「9·11」、校园枪击案,更别说全球变暖和战争。在我统计之列的2008年,还爆发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但数据没有显示出这种关联性。2012年之前,所有人的心理表现都很平稳,2012年之后,出生于1946-1964年的婴儿潮世代的数据波动并不明显,1965-1980年的X世代甚至还有小幅下降。心理疾病的增长独属于Z世代和出生较晚的千禧一代。后来,我持续追踪了这部分数据,发现到了2020年,每四名美国少女中就有一人经历过抑郁发作。2021年,情况继续恶化。
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一部分孩子可能真的是过于敏感,但综合来看,在过去这十年间,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严重影响了这一代年轻人的生活。
那让我们再看一组数据吧——2007年,苹果推出了第一部智能手机iPhone,从此所有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上网。2010年,手机第一次配置了前置摄像头。到了2012年,Facebook成功收购了Instagram,之后它的用户数量出现爆发式的增长。2013年左右,大多数青少年都已经拥有了智能手机,也已经在用社交媒体。2015年,尤其是女孩儿们,手机里几乎都有Instagram。只有这一条时间线年代末的孩子,就是历史上第一批在虚拟世界中度过青春期的人,他们的社交模式、行为榜样、情绪状态、体育活动,甚至睡眠习惯,都因此经历了根本性的变革。

我住在纽约,这里的大部分家长会等孩子到小学四五年级才让他们试着独自上下学。我们家努力把这个起点提前了一两年,原因是我结识了学者兰诺·斯肯纳齐( Lenore Skenazy ),2008年,她在报纸上撰文讲述了她9岁的小儿子独自乘坐地铁的故事。在文章里她写到:「一半知道这个故事的人都想以虐待儿童罪起诉我。」在文章外,她落了一个「全美最差劲的妈妈」的外号。
2009年,我看了她写的《放养孩子》,不得不说,她说到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存在很久了,但大家一直都没当回事。我和妻子曾派儿子去街对面的超市买东西,其实也就是穿过一条马路,但回来后,儿子说他感觉不舒服,因为他是超市里唯一一个这么大的孩子,所有人都在看他。
我和妻子下定决心,必须要送孩子出门。他先是多去了几次超市,不舒服的感觉好了很多,我们作为大人的感受也好了很多。到了他9岁的时候,我们又前进了一些,让他步行去上学。
虽然我家离学校不到一公里,但我和妻子还是安排了一个逐步脱敏的过程。最开始是从我们骑车接送改成步行,儿子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我们不交谈,我也不会告诉他哪里该拐弯,哪里继续向前。这么走了两三次后,我让他自己试试。我们把一台旧iPhone给了他,并打开查找权限,可以实时看到他的位置。
但他真正走出家门的第一天,我和妻子很恐惧,心脏砰砰跳,整个人都特别紧张,直到看到那个代表儿子的小蓝点终于拐进了学校。第二天就容易很多了,第三天更轻松,后来我们就不再盯着手机上的实时追踪了。他很快熟悉了那一片街区,也很快就了解了纽约的地铁系统。到了我女儿9岁的时候,我们给她配了一块能打电话的手表,也让她出门去。
相对其他家长,我们把孩子独自出门的时间提前了一两年左右。在此之前的大多数童年时间里,他们都被保护在家长的视线范围内。
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放学就是去外面,玩耍,大家都是如此,没有大人看管。即使到了上世纪90年代,交通法不算完善,城市犯罪率也比现在高很多,但大部分人都会让孩子尝试独自长大。
我把以往这种童年模式称之为「玩耍式童年」。自由玩耍的过程中,孩子们每天都有新体验,边玩边学,各种能力就这么一点点掌握。这其实也是大脑慢慢发育、搭建神经通路的过程。特别是在和很多小伙伴一起玩的时候,他们通过聊天、开玩笑,学着察言观色,捕捉别人的微表情和肢体语言。有时候话说错了,还得学着圆场,把气氛缓和回来。这些都不是谁教的,就是在相处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如何把握分寸。
回忆一下以前的游乐设施,像是那种巨大的攀爬架、转得飞快的转椅,看着就令人汗毛直竖,如果有小孩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绝对要受重伤,搞不好会有生命危险。放在现在,估计没几个家长敢让孩子玩。可我们这一代代不也这么长大了?其实在孩子的玩耍里,危险没那么可怕。他们喜欢冒险、寻求刺激,比如玩火、爬高下低,甚至打起来,这些背后,是大脑中的「发现系统」在起作用。正是在这种探索里,他们才慢慢摸清自己能力的边界,学会识别危险、处理问题,并且不怕犯错。哪怕不小心受了点小伤,他们也能自己搞定,不用动不动就喊大人。
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少经历这些。上世纪90年代,从中上层家庭开始,美国人就逐渐转变了这种自由放养的养育模式,盘旋在孩子头顶上空的「直升机式父母」越来越多。
这种转变有它的时代背景:大学录取难度逐年都在提升;新闻开始使用标题党危言耸听,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孩子们也被困在了大门内。整个社会氛围都在不停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多么危险,千万不要以身试险、不要陷入纠纷、不要试图去找什么乐子。和过去孩子那种爱探索的天性不同,这一代孩子开启的是「防御系统」,对潜在的风险特别警觉,整个人也显得特别焦虑,戒备心拉得很满。
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对孩子管教严格、保护过度,担心种种绑架或者性侵犯,但相对而言,在网络世界里,人们疏于监督,对孩子保护不足。在智能手机之前,真正走向歧途的代价是高昂的,可如今任何一个12岁的男孩,只要他想,他就能找到免费看色情内容的地址,甚至大多数针对儿童的性犯罪者也是活跃在线上的。
很久之前,我和美国主流社交媒体Snapchat的首席执行官聊过,他告诉我,Snapchat是朋友间用来说话的,和短信一样,只是增加了图片功能。「就只是朋友们用来玩的。」他是这么说的。
「那可能情况也不是很糟糕。」我当时想。毕竟大多数社交媒体都设有用户年龄限制和净化门槛,法律也规定了注册最低年龄。但等我开始做研究,才发现根本不是我想的那样,我随意用儿子的姓名注册了账号,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对用户年龄的审查。事实上,所有公司都不会真的这么做,因为这就等同于把新用户拱手让给竞争对手。
更恐怖的是,从我注册成功开始,Snapchat就一直在给我推各种不认识的人,让我加他们好友。它似乎是试图在让我和儿子圈子里的每个人都建立联系,但那些人并不全是他的朋友,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人。Snapchat上也有低智小视频,很多甚至带有侮辱性。
在社交页面,Snapchat也在致力于给我推泳装美女。我注册账号的时候我儿子13岁,在这个原本应该是13岁男孩的主页里,就这样自然而然出现了这么些性感的画面。
根据2019年的一项数据统计,青少年每天耗在电子屏幕上的时间是6~8小时。另一项国民研究表明,有近一半的青少年表示自己「几乎不间断」地上着网。在「玩耍式童年」退场之后,如今的孩子们,正在经历的是「手机式童年」。
网上时间多了,意味着现实时间少了,人们面对面交流的亲密度大打折扣;孩子们的睡眠时间也变少了,睡不够或睡不好也进一步可能导致抑郁;注意力变得碎片化,有研究表明,手机式童年也正在加剧ADHD症状。孩子们对手机上瘾,在社交媒体中追求更多人甚至陌生人的认同和肯定。
旧有的童年规则不再适用,新的秩序还没建立起来。当这股技术洪流在2012年左右开始席卷世界时,孩子并没有准备好。

研究中我还发现,很多数据会在性别上表现出差异,概括起来,就是孤独的男孩和焦虑的女孩。
对男孩来说,转变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欧美经济重心转向服务业,男性的能力和地位就开始下滑。因为在很多服务型行业,女性会更有优势。甚至从学校开始,女生的成绩就普遍比男生好。再加上能自由玩耍的童年消失,新一代的男孩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回避现实。
智能设备的出现恰到好处。它给男孩们提供了一条退路:既然在现实里这么焦虑又挫败,那不如就躲进虚拟世界。他们在网上重新找存在感,打打杀杀的游戏、刷不完的视频,还有越来越直白的色情内容。一切「快乐」都藏在这块电子屏幕里,并且这块屏幕还越来越小、越来越便携了,让人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泡在上面。
全球范围内,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退出」的趋势,比如美国,常用「没能成功起飞」来形容那些脱离正轨、找不到工作只能回家啃老的年轻人,其中男性占了大头。日本则有以男性为主的「蛰居族」,还有一些号称「不欢迎女性」的网络论坛,里面的人往往既傲慢又偏激。
当男性饱受网络游戏带来的影响的同时,女性依旧在现实世界里挣扎,她们遭受「社交媒体成瘾」的概率明显比男性高。
社交媒体利用了女孩的恐惧和兴趣。2022年,一对父母把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告上了法庭,控告这家公司未经父母允许,擅自向他们的女儿提供有害的产品。女孩亚历克西丝在11岁那年注册Instagram,她在注册信息上填了13岁,一路畅通无阻。
起初,每一个新增关注都令她感到开心。但很快,应用为她推荐的内容从一开始她喜欢的健身信息,变成了模特的照片,又变成了节食的建议,最终是传播厌食倾向的内容。注册5个月之后,亚历克西丝画了一幅自画像,「谣言、废物、没人爱你、肥猪、怪物、笨猪、神经病」等负面词汇包围着她。8年级时,亚历克西丝因厌食和抑郁住院。
父母尝试过让她脱离Instagram,但亚历克西丝总是用完即卸载,完全不留痕迹。她学会了把图标隐藏,或者创建小号,继续悄悄地发布内容。余下的青少年时期,她都在持续与两种疾病做斗争。
数据上能看到,2012年以后,美国女孩们明显变得更容易情绪低落了。调查显示,每天刷社交媒体超过5小时的女孩,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是完全不用的女孩的3倍。和男孩相比,女孩在这种无休止的「比较」里更容易受伤。社会好像总是在暗示甚至要求她们必须追求完美,而社交媒体又清清楚楚地告诉她们:什么样的生活更体面、谁更受欢迎、什么样的长相才算美、现在又在流行什么……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对她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即使不想跟风,女孩们也很难退出,因为这和现实社会相挂钩。与直接的暴力行为不同,女孩之间的攻击性更多表现为散布谣言和挑拨关系,社交媒体在其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必须意识到的一点是,以上种种并不全是孩子们、家长甚至互联网的错。即使在手机出现之前,我们也不是没有分心过。人脑本身就受多巴胺影响,这是我们人体构造的一部分。
我强烈谴责的是那些掌控童年并拒绝给孩子们提供保护的科技公司,他们明明可以做更多,但就是死守着所谓的「用户黏合度」。巨头们在虚拟世界里创造了空前的繁荣,但发展的成果并不会被现实世界共享。
现实就是这样,手机几乎打败了所有其他选择,让所有东西都变得太容易得到了。现在AI还掺和进来,情况变得更糟。在这个环境下,阅读、写作、安静思考、认真做计划这些真正能让人进步的事,做起来特别难。
依赖手机的生活方式,会在不知不觉中消耗人的精气神。这一代年轻人看起来生活被手机填得满满的,可心里却总是空荡荡的,有种说不出的虚无感。如果我们还放任他们把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经筛选地往这种空虚里硬塞,结果可想而知——我们只会看到一群被孤独和焦虑困住的孩子。

每当我提议推迟孩子接触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年龄,常常听到这样的回应:「我赞同,但似乎为时已晚。」
这是智能设备时代的另一种挑战:很多孩子用手机,其实是怕被孤立、怕落单。这不光是孩子自己的难题,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困境。
在智能手机刚出现的时候,谁都不会想到它能发展成这样。可一旦风气形成了,这已经不是单靠哪个人努力就能解决的了。就算有父母想逆流而上,不让孩子用手机,结果可能让孩子在同学中更被孤立;哪怕有些科技公司真想做出改变,他们也会马上看到用户流失、数据下滑。
但我仍然觉得,「为时已晚」未必是一个合适的说法,要知道,人脑的额叶皮层直到25岁左右才完成自身的构建,大部分的年轻人依旧有时间去改变这一切。另外,我知道有些家长在做抵抗,他们设立了严格的管控,不仅给孩子报名夏令营等各种活动,甚至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全家一起出游,度过一个无手机的周末。但这同样是一种「过度保护」式的养育,并且成本非常高——父母不仅要花很多钱,还要投入大量时间,这对现在主流的双职工家庭来说,真的很难实现。
相比之下,「放养」会便宜很多,也能让孩子重新回到那种「在玩中学」的状态。其实只要有几个孩子一起,他们自然就能互相作伴、彼此支持。我一直觉得,想办法让七八岁的孩子能聚在一起自己玩,这点特别重要。没有大人站在旁边,就他们自己。
最简单的就是重新建立和附近的联系。我知道,现在大家都不太认识邻居了,但那扇门,我们还是可以去敲的。作为家长,我们可以主动开口打个招呼:「你好呀,你家孩子想一起下来玩吗?」
假设转了一圈后,我们拉来了一共5个家庭,大家的孩子年纪都差不多。大人们可以每周约好一个或多个固定的时间,比如周五下午,或者周末晚上,一起放孩子们出门,让他们在小区甚至街区里跑来跑去——去这家敲门喊人出来,然后再一起去下一家玩之类的。等孩子们熟悉了这种模式之后,大人们也可以看情况给他们一些零花钱,这样他们就可以再一起去买个冰淇淋了。再之后,邀请朋友来家里过夜也就顺理成章,但这里要注意,尽量和孩子们说好,都不要带手机来。
今年3月,我和团队又做了一次调查。在接受访问的500多个孩子里,有45%的孩子选择了「希望能自由地和朋友们面对面待在一起」。有将近3/4的孩子都同意这句话:「如果我住的附近有更多朋友能一起玩,我就会花更少时间上网。」
这说明,想让孩子出门玩,并不是大人们一头热,孩子们自己也同样期待能有伙伴一起。所以,在帮孩子少玩手机这件事上,家长不妨试着主动迈出第一步,去认识认识邻居,也多给孩子一些信任。孩子没有现实中的玩伴,是现在很多家庭都要面对的难题,但只要我们多找几个人一起行动,这件事其实就没那么难。
让我挺高兴的是,在现实里已经看到一些类似的尝试了。比如有些学校设置了手机袋、手机保管箱,努力打造一个不用手机的校园环境;还有些小学特意增加了课外活动时间,允许孩子们进行一些没有固定规则的玩闹;一些儿童游乐场也有意识地保留了木材、石头、水这些天然材料,让孩子们不必只在水泥地或橡胶地上玩。
还有一些家长开始牵头组织「8年级手机联盟」,约定好在8年级之前不给孩子使用手机。并且,这个联盟必须要求10个及以上的家庭签署,以此保证有足够的孩子在一起,避免被孤立。不过在我看来,8年级还是太早了,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会有一版建议,我非常赞同:
未满18个月的孩子,原则上不能使用任何智能设备,但可以与大人进行一对一的视频聊天,如与不在本地的父母进行视频交流。
2~5岁的孩子,非教育类的节目和应用程序,工作日每天最多可以观看1小时,周末每天最多3小时。
16岁之前的孩子,尽量避免开设社交账号。这也需要科技巨头也加入这场全社会斗争中,行业应该形成明确的准入基准。
不要将智能设备作为安抚或陪伴工具。孩子闹情绪时,父母不要习惯性地用智能设备去哄孩子。
作为带过孩子的人,我其实完全理解:当你一边准备晚饭,一边应付工作电话,或者仅仅是想休息几分钟时,如果没有电子设备帮忙,那真是难上加难。我和我妻子就曾经常用《》来稳住孩子,让他从婴儿时期一直看到幼儿阶段。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们肯定不会再用这种方式了。
远离手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应该形成这种共识。在我看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每天刷社交媒体的时间最多半小时,这应该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不要用要在手机上处理工作或者事物为借口,把那些能在电脑上处理的放在电脑上,然后让你的手机和脑子都休息一会儿。